父子作家与鄂尔多斯
转自:农民日报

肖亦农与肖睿。

肖亦农(左一)在生产建设兵团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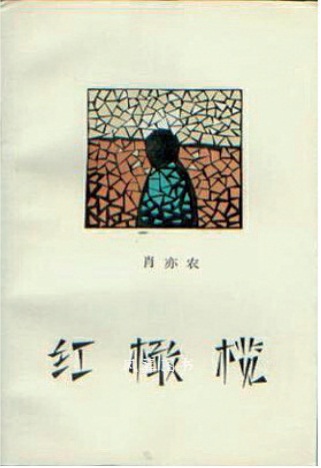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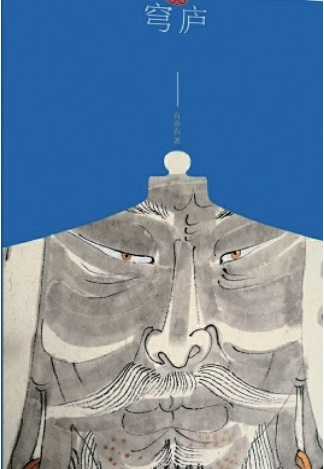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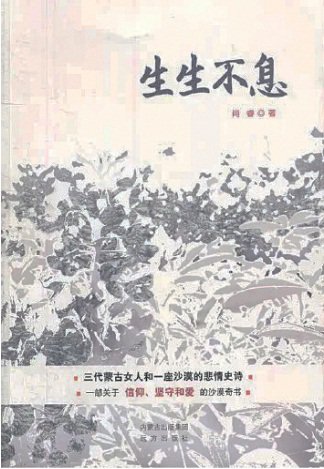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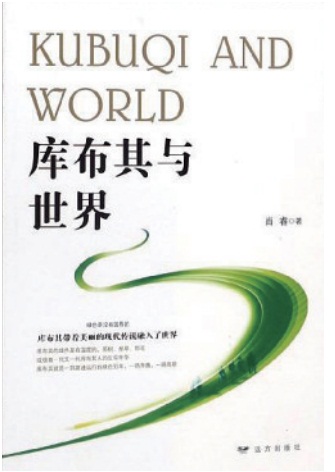
肖亦农,祖籍河北保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代表作有八卷本文集——《肖亦农金色弯弓系列》,包括《红橄榄》《灰腾梁》《孤岛》《天鹅泪》《我的鄂尔多斯》《黑界地》《长河落日》《爱在冰雪纷飞时》。作品《毛乌素绿色传奇》荣获全国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其作品还曾获《十月》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2010年获内蒙古自治区文艺创作突出贡献奖。
肖睿,青年作家,1984年出生,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代表作有《生生不息》《库布其与世界》《打雪仗》《一路嚎叫》等,曾获夏衍杯电影文学奖首奖、索龙嘎文学奖、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这块土地就是我,我就是这块土地。
真正的作家,就该有这么一种情怀。
见到肖亦农,刚落座,他说:“你还写啊?”估计他是凭年龄在判断。他又说:“我不再写了,前年心梗后,就不写了。”
我说:“不要不写,写点小的,练脑,别痴呆了。”
他说:“你这个说法好,想写时写写,也不能不写。”
我说:“当时我们的计划,是让你写你的。”
他笑笑说:“可不能让我再写我。当年,刘震云与我同时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毕业,他还在你们报社,他约过我写稿。结果,我拖了四五个月没有完成任务,刘震云当时非常‘生气’。现在你来了,我得说实话了,我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你了吧?”
肖亦农在全国知名作家群里,是有名的生态文学作家。他写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写生态文学作品,是后来的事儿了。他说,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一
肖亦农17岁就来到了内蒙古伊克昭盟(现在的鄂尔多斯市),进入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几年里,他目睹了这里的穷困与沙漠化的严重。“出门是沙,回家还是沙。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常常门窗紧闭,屋里也到处都是沙子。很多时候,外面连续狂风呼啸,屋里地上、桌子上落下黄黄的细沙。就是吃饭中间,嘴巴里也咯咯吱吱嚼上了沙砾。”这是他最为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参加工作是在交通部门,依然还是摆脱不了沙漠的纠缠。每一次修路,也多是和沙漠在较劲。这样的现实经历才引发了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注意。
在兵团时,肖亦农就开始写小说了,但他说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考虑怎样把生态环境问题上升到创作中,作品还多是那种青春和伤痕文学题材。
他从兵团招工到了盟(市)交通局,刚一上班,就被分配到了一个偏远的公路养护道班。道班孤零零的,周围没有什么住户,只有黄沙漫漫。每天沙漠的奇特现象,对外人的感觉是新鲜和激动,但对久居沙漠的人,却是那么的无奈与叹息。“往往白天我们屋门还畅通无阻,到第二天早晨,你很难推开房门,人得跳窗出去清理积沙。”肖说,“后来,路过的牧民到道班歇脚,介绍了许多防沙做法,比如修了院墙大门,并围着院墙种树等等,建起了一片片副食基地、小苗圃,还挖了一个小鱼塘。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漠里的牧民的经验,起到了关键作用。不然,你无法在沙漠中生存下来。当然,人与沙漠的抗争中,还是能战胜沙漠的肆虐的。吸收牧民的经验,道班养护的沙漠公路,始终保持着通畅。”
肖亦农只在道班工作了一年,但他所在的道班被彼时的交通部命名为“红旗道班”。至今,他说起来还是骄傲不已,不仅因为荣誉,更因为现实也回答了他,恶劣的环境虽可怕,但人类能够改变它。他以这个英雄群体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灰腾梁》和短篇小说《山风》。这两篇作品都被《小说月报》转载,并被收进多个选本里,成为肖早期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
有一年单位植树,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小白杨树,还在树身上刻下了一行字。过后的第30年,他专门领着《十月》当时的主编张守仁先生在一片荒漠里找到过它。那时它已经长得碗口般粗细了,那刻字还依稀可辨,肖不禁泪眼婆娑。
“当时,张守仁先生曾抚摸着大树对我说,以后的创作主题,有可能要立足生态问题。”他的这句话,肖亦农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张守仁之所以专程去往鄂尔多斯,是听了肖讲“黄河船夫曲”的创作故事,而受到感染。肖说,本来想写一个短篇,张觉得应该至少写成中篇。那年,张在鄂尔多斯待了下来,他们一起研究构思、立意、结构及通篇布局,甚至许多细节等。为了更生动更形象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深入牧区乡村和草原深处,尤其是沿黄河一带采风,吃住几乎都在农家,行程达到上千公里,终于完成了这个中篇小说。
如今,肖亦农还是会时常想起那棵白杨树,这棵树其实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文学之树。
几十年后,肖亦农说起这段经历时,依旧目光如炬。他又回到我们刚见面时的对话,感叹说:“我还不能放笔,还要写下去,鄂尔多斯是写不完的主题。”
我也被他感动,要知道,他现在已经七十有二了。
二
到北京见肖亦农之前,网上一篇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今年刊登在第七期《人民文学》上的一篇中篇小说,作者叫肖睿。路上我就一直猜测,“不会是肖亦农的儿子吧?”见到肖,我问他,他说是。
本来是奔着肖亦农而来,没想到,他还没有聊自己,却先给了我一个新收获和意外惊喜。聊到儿子,肖亦农格外激动,开心和骄傲就在眼睛里打转。
翻开这第七期的《人民文学》,中篇小说一栏只有两篇,其中《库布齐诗篇》赫然在目。不用再问,在内蒙古生活多年的我,知道这是写内蒙古。这期除了刊登这篇小说,杂志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因其聚焦重大主题、体现地域特色和文学构思精巧,先后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大字版》等多家知名文学刊物转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业内好评,为新时代内蒙古生态文学创作增添了亮丽色彩。
库布其沙漠,就位于鄂尔多斯市。肖亦农在兵团时的位置,就在库布其沙漠深处。
看肖睿这个中篇小说,我一下子有被“抓进去”的感觉。怪不得不光是《人民文学》刊发,好几个著名文学杂志还都转载了这篇小说。
肖亦农说,肖睿二十岁时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他发现儿子突然不写了。儿子说写不下去了,没有了创作灵感,感觉创作素材一下子枯竭了。
“当时,我的创作也正在热火朝天中,没有过多理会他(儿子)的这个变化。”肖说,那些年,儿子一直在北京和他生活,这也许就是他不写的一个原因。
他说,肖睿从小就喜欢文学,后来立志与文学相伴到老。为此,肖睿还下定决心要做纯粹自由撰稿人。“怎么才二十多岁,正在起步期间,就要打退堂鼓了?”他当时判断,北京大都市的生活可能已经改变了儿子的思维与习惯。他认真研究了肖睿先前的作品,几乎和他年轻时一样,还徘徊在城市青春文学的层面上。
肖亦农属于那种不善言辞之人,他说,对于儿子的变化,不能靠说教去改变他。
他放下自己的创作,找了个机会,领着儿子又回到了鄂尔多斯。那年,儿子已经快三十岁了,他离开鄂尔多斯也十几年了。这期间,库布其沙漠也在发生着许多变化,已经有了好几处“绿洲”了。这让肖睿意想不到。这里的人们锲而不舍治理沙漠的决心和成果,时时震撼着肖睿的心灵。特别是涌现出的“种树种到联合国”的王果香、因为种树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殷玉珍等典型人物事迹,更让肖睿茅塞顿开。这里环境的每一个变迁,都引起了肖睿无尽的好奇和感慨。尤其是高科技治沙设备的引进,更是触动了他的灵感。有一次,他看到这里利用无人机飞播治沙,只5秒钟后,树种便装填完毕,手一按遥控器,几架甚至十几架无人机随即盘旋在库布其沙漠上空,在总面积1.41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也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上播撒绿色。
肖睿从创作感到枯竭,到激情澎湃,父亲的引导至关重要。
肖睿回来的那几年,从无定河到黄河,从七星湖到乌审召,从穿沙公路到萨拉乌苏河谷的专题采访,使他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全景式地展现了库布其治沙史。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新时代生态文学力作,也是一部深入开掘库布其儿女心灵史,具有独特文学性和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认识沙漠,借鉴世界很多国家开发利用沙漠资源的经验,创造和传播中国治理荒漠化的模式,正是库布其人民多年的努力。肖睿琢磨,文学创作怎么与世界对话?这是一个新的尝试。他的作品里写到多年来一直研究库布其沙漠的意大利姑娘卡萨努等外国青年朋友,多次与他们一起进入库布其沙漠考察,展示了年轻一代开阔的生态视野,以及库布其将世界揽入怀中,并与世界融为一体的真实现实。
从小见识过沙漠威严的肖睿,如今感受到沙漠变年轻了,而那些治沙的人们却都变老了。他形容这些治沙人就像沙漠上的黑橄榄树,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身子挺立在沙漠上,迎着雨雪风霜,狂风烈日。
他采访一位机械化造林总场的分场女场长,“她是一位年届50岁的阿姨,因为长年风吹日晒,她的皮肤异常干燥粗糙,声音沙哑,但性格极为豪爽。阿姨对我说,在库布其林业工作的人,简历都极其简单。就像我吧,33年就一行字:1984年大学毕业,进入鄂尔多斯机械化造林总场至今。”这位女专家说,“在你的书中多写树就行,我的儿女就是库布其的树,我是它们的母亲。”
这样的描写在书中不胜枚举,每每写到动情处,肖睿会情不自禁眼含热泪。他记录了莫日根道尔计、徐治民、田青云、高林树那些默默无闻的人,还讲述了当地名人赵永亮与风水梁,王文彪与七星湖的故事,以及孟克、茹力玛、刘雪芹一大批为了库布其奉献青春的年轻人,在他的笔下,他们都是库布其的英雄,他们有多平凡,就有多伟大。
肖睿在对人物的了解中,经过多方位的分析比较,发现采访越多,接触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材料越多,也就越绕不过一些难写但必须写的人物。“他们在我的这本书里,只不过是无数非虚构文学人物中的一个,亦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他们在库布其沙漠,却像一座山一样存在着。我写他们,山存在;我不写他们,山也存在。他们并不因我写不写而增高一分或低矮一寸,也不因我写不写变得高尚或龌龊。”
肖睿认为,从感性到理性,才能更好展示出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库布其模式”,梳理和探究现代工业化、科技化与库布其沙漠的未来,从而体现中国生态理念对于世界的意义,也显示出作家的情怀与担当。
肖亦农说,肖睿也不算年轻了,马上就到四十岁了。我说,对于作家来说,还属于年轻一代。
肖亦农获奖的报告文学,写的就是治理沙漠的真实故事。肖亦农说,通过言传身教,传统的“战天斗地”和现代科技的结合,让肖睿大开眼界,他的灵感如飞,他无法再坐下来,立刻创作了他生态文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生不息》。
“他的创作热情再一次被激活,那年他正好三十岁。可以说,这是他的运气。”肖亦农这样说儿子。也可以说,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国文学界多了一对专门关注生态文学的父子作家。
肖睿的生态文学,最大的亮点在报告文学创作上,这与其父亲十分相像。肖睿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在体验沙漠生命的同时,个人的感悟也在不断升华。“我在库布其沙漠采风时,不管是接触世界级的治沙大师还是采访最平凡的植树者,都会有一种感受——他们面对沙漠、面对孤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干着一件在沙漠上‘铺绿’的事情,的确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来支撑。我忽然觉得,自己的生命既是古老的又是新鲜的。千万年的痕迹留在了我的灵魂中,可每一次呼吸又是崭新的,充满了活力。是库布其沙漠给了我力量,并给了我强大的信心。”
肖睿的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走进社会与读者互动,不同程度影响着大众对生态文学的认知。“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这样的创作环境。”肖亦农这样评价。
三
肖亦农1969年作为知青来到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又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从鄂尔多斯走出的作家,这片热土赋予他文学创作的营养。他在鄂尔多斯生活了半个世纪,见证了鄂尔多斯的发展。
肖亦农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金色弯弓》系列小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篇《孤岛》刊发于1987年第五期《十月》杂志头条位置。当时的《十月》主编张守仁专程来到鄂尔多斯,肖亦农正好把刚写完的新作《红橄榄》给他看,张守仁读后激动不已,很快就发表在1987年的第六期头条上,随即轰动全国。那年,肖亦农算正式进入全国一线作家的行列。同年,他又在《十月》发表了第三个头条,中篇小说《灰腾梁》。一个作家一年之内发三个头条,这在《十月》历史上绝无仅有,肖亦农成了内蒙古的骄傲。内蒙古作家协会在鄂尔多斯召开肖亦农作品讨论会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和内蒙古作家协会所有领导参加了研讨,成为文坛一件盛事。此后,肖亦农进入了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继续深造,李准、童庆炳、谢冕等文学大师都是肖亦农的导师。回忆这段求学经历,他说,任何人的成功都离不开读书。
肖亦农用七年的时间完成了“金色弯弓”系列小说的写作,二十多部小说先后发表在《十月》《当代》《人民文学》等国家重要文学期刊,并被多种选刊转载。这一现象被称为“文坛刮起了草原旋风”。
那时,他虽然是在写知青生活,但几乎每一篇作品里面,都隐隐约约透露着知青与牧民之间的情感交织,许多环境描写离不开草原、沙漠和牛羊。比如他写的电视剧《我的鄂尔多斯》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他看了“丹丕尔抗垦”这段鄂尔多斯的历史,了解到这里曾经还是“走西口”的主要过渡地。因为走西口,使这块草原人口增加,经济活动频繁。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在肖亦农的心中生根发芽,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黑界地》,四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情节跌宕起伏、思想肆意徜徉、气质大开大合的著作。文学期刊《小说家》以整期刊物的篇幅发表。
几十年过去了,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依然在读者心中熠熠生辉。《黑界地》让鄂尔多斯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座“重镇”。肖亦农从一个著名作家变成了鄂尔多斯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创作因此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意义与历史意义。
那一年,当肖亦农看到,由于坚持不懈地治沙,绿色成为了毛乌素沙漠主色,沙漠甚至要从地图上消失了的报道,他顿时意识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课题。他一口气写了长篇、中篇等几十部报告文学,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这些作品奠定了他生态文学作家的地位。“这块土地就是我,我就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作家,就该有这么一种情怀。”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诗人郭小川来到鄂尔多斯,创造出了很多传奇,推出了全国“牧业学大寨”宝日勒岱“人定胜天、改天换地”的先进典型和经验,这给了他无尽的动力和创作想象。
肖亦农动情地说:“鄂尔多斯沙漠翻天覆地的变化撞击着我,感动着我。实际上,我的创作激情是从鄂尔多斯大漠中长出来的,真不是采风采来的。因为我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我熟稔的朋友,我从来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不过是在荒漠化治理的伟业中有不同的分工罢了。我感谢鄂尔多斯大地给予了我那么多的创作灵感。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就足够你展示文学才华和文学抱负了。”
他的另一个长篇小说《穹庐》,历时12年才得以完成。肖亦农认为,挖掘蒙古民族的民族性是他的文学使命,他发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民族性的两大支撑,而《穹庐》中布里亚特东归祖国的故事,正是这两大精神的体现。作品完成后,《十月》决定整期刊物单独发表这部长篇小说,这还是《十月》创刊以来的首次。《穹庐》当年入选中国多个重要的长篇小说排行榜,并获得了《十月》杂志当年的文学奖。
肖亦农认为,一个作家要研究自己站立着的土地的历史与文化。他佩服巴尔扎克深耕巴黎,敬仰托尔斯泰足不离波良拿小镇而将广袤的俄罗斯托于掌上,喜欢莫言用一支大笔建立的斑驳高密。“‘用心’,是一个沉甸甸的词语,值得作家反复咀嚼。作家用心思考,用心写作,将心交于读者,甚至将自己的血肉与自己生活的土地融为一体,你的心脏随着土地的脉搏而跳动,你的喜怒哀乐随着这块土地上人民的生存状态而翻滚起伏,你才会懂得为人民写作的分量,才会懂得构建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学的神圣与庄严。”
四
与肖亦农聊天时间并不长,但他几次说,人要有骨气,骨头要硬。这是作家的标配。“你没有骨头,当不了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还担任鄂尔多斯市交通局副局长。那年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同路人》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准备拍电影。但因为题材反映的是交通领域腐败问题,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反对,终被叫停。有人不理解他,说他丑化了交通人。至于文学创作的虚构性,更不会有人明白。他说,交通腐败那时很严重,“比如十厘米的基础改八厘米,那得有多少钱消失”。那时,每天晚上他都紧闭院门,来人怎么敲都不开。
他说他这个人很笨,连微信发位置都不会。我到北京能找到他的位置,还是他让别人操作发给我的。
我们道别时,他执意要请我吃饭,但被我婉拒了。他问我喝不喝酒了,我说基本不喝了。他说他也不喝了。这要在过去,今晚这个饭非吃不可,他说。看我不解,他说他那时可是有名的“肖不倒”。我说,那时你是“喝”不倒,现在,我希望你是真不倒,特别在生态文学创作上,继续你的辉煌。他说,努力吧!虽然我们都老了。
(作者系农民日报社内蒙古记者站原站长)
版权声明:本文系农民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致电010-84395223或回复微信公众号“农民日报 ID:farmersdaily”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如有侵权,本报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