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鲁滨逊漂流之后,弗兰岑把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带去了那处秘境岛屿
转自:上观新闻

近期,美国小说家、随笔作家乔纳森·弗兰岑随笔集《更远之地》,由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引进出版。
该书收录弗兰岑所撰写的演讲文稿、纪实特稿、书评等文章,涉及阅读与创作、环境保护、社交媒体成瘾与滥用等切身紧迫的议题。
对于弗兰岑来说,最重要的是真实,是爱,确信自己坚信的,然后去捍卫,确信自己不满的,然后去反驳。温和、讨好从不是弗兰岑的形容词。
这本书呈现了一个态度鲜明、满怀热爱的人如何介入世界、参与世界。真实的爱可以掺杂着痛苦,但痛苦毁不了你的人生,而最终定义我们的,是我们所热爱的、憎恨的,让我们为之激动的一切。
Farther A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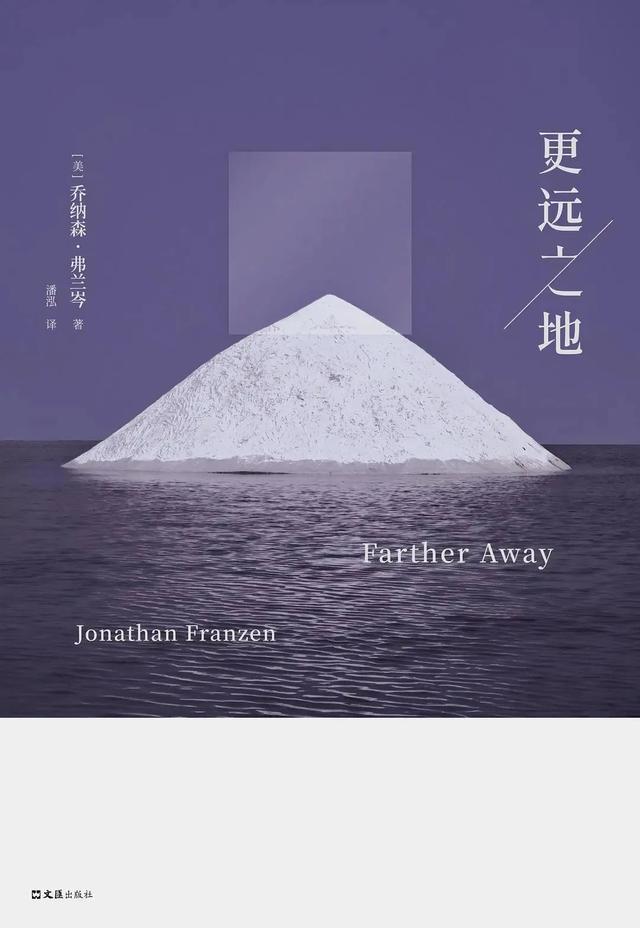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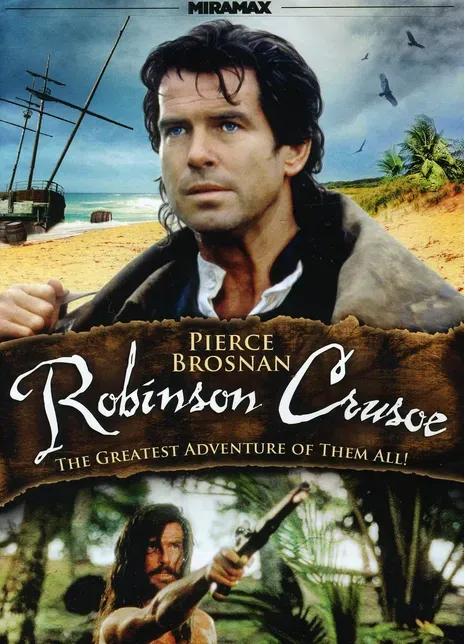
远方(节选)
我首次接触到《鲁滨逊漂流记》,是小时候父亲念给我听的。这本书加上《悲惨世界》,是仅有的两部他喜欢的小说。从他读给我听时那陶醉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对鲁滨逊和冉阿让产生了同等的深切认同感(不过他把冉阿让读成了“金发吉”,这是他自己琢磨的发音)。和鲁滨逊一样,我父亲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很疏离,生活起居克己简朴,深信西方文明比其他“野蛮”文化优越得多,认为大自然应该是人类征服和开发的对象,无论遇上什么事情他都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去做。这个独自栖身于荒岛、被食人族包围的人自律拼搏求生存的故事,对他来说实在是再浪漫不过了。
.......


我十六岁的那个夏天,机会终于来临,父母答应了我的央求,让我去参加一门名叫“西部野营”的暑期课程。我和朋友魏德曼就这样跟一车同龄少年以及几位指导老师一起去落基山脉“调研”了两个星期。我背着汤姆用过的格里牌红色旧背包,随身带着汤姆也有的那种笔记本,用来做研究苔藓的笔记,那课题是我胡乱挑的。
我们到爱达荷州锯齿荒原的第二天,就被要求到野外独自度过二十四小时。我的指导老师把我带到一片稀疏的西黄松树林里,然后就让我一个人留在那儿;没过多久我就蜷缩在我的帐篷里,尽管外面风和日丽。显然,短短几个钟头没人做伴,就使我完全感受到了生命之空虚,存在之恐怖。第二天我才得知,比我大八个月的魏德曼不堪忍受如此孤独,自己提前回到了大本营附近。而能让我坚持下来,甚至能让我觉得我可以孤身一人度过一天以上时光的原因,就是写作。
......

在距智利中部五百英里左右的南太平洋里,矗立着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火山岛,七英里长、四英里宽;岛上栖息着数以千计的海狗和数以百万计的海鸟,但人迹罕至;每到暖季,只有零星几个渔民来此捕龙虾。要去这座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的岛,得从圣地亚哥坐飞机——那种只有八个座位的小飞机,每周只有两班——先到位于其东面一百英里的另一座岛,再从岛上的停机坪乘敞篷小船才能到达整个群岛里唯一的村落,然后在那儿等,等着搭乘偶尔出海的船,从那儿去塞尔柯克岛单程就得花十二个小时,就算到了跟前通常还得再等,有时一等就是几天,得等到天公作美才能登上那座岛的岩岸。
该岛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智利旅游官员更名为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岛的,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多半就是根据这位苏格兰水手在这群岛上的孤独漂流生活写成,不过当地人还是用原名来称呼它——马萨弗拉,意即更远的地方。

去年秋末时,我起念要到某个更远的地方去。当时我已马不停蹄地参与一本小说的推广活动达四个月之久,每天都是按安排好的行程度日,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媒体播放器进度条上那个往前挪动着的菱形标志。我不断复述自己的人生,结果是大段大段重要的个人经历在内心殒殁。每天早晨都是从相同剂量的尼古丁和咖啡因开始;每天晚上我的电子邮箱都受到同样的狂轰滥炸;每天夜里都是同样用酒精来麻痹大脑换得一时的欢愉。其间,在某一时刻读到了马萨弗拉的相关信息后,我开始想着逃离,独自逃到那岛上去,像塞尔柯克那样藏身于全年杳无人迹的内岛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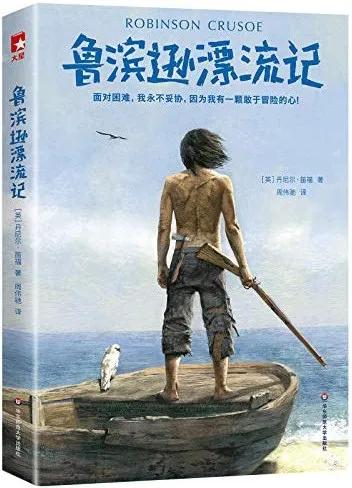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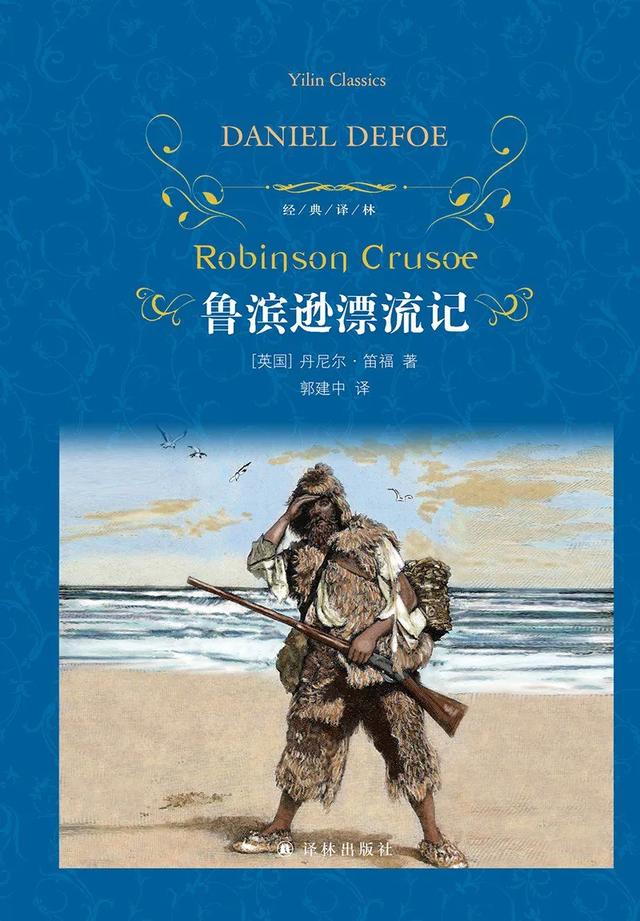
《鲁滨逊漂流记》
我还在想去那岛上待着时,把《鲁滨逊漂流记》重读一遍应该感觉挺不错的,那可是公认的第一部英文小说。这本书是对极端个人主义的伟大的早期记录,讲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普通人以全副身心拼搏、挣扎求生的故事。接下来的三百年间,这种以现实主义叙述手法来探索生命意义、以个人主义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在我们的文化里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形式。我们可以从后来的简·爱、地下室人、隐形人以及萨特笔下的洛根丁嘴里听到鲁滨逊的声音。
这些故事都曾让我激动不已,难以忘记年轻时静静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被小说顾名思义的新奇所吸引而孜孜不倦、全神贯注的经历。伊恩·瓦特在他的经典著作《小说的兴起》里指出,十八世纪小说出版的迅猛发展,跟家庭妇女居家娱乐需求的增长紧密相关——那时的妇女已经从传统的家务活里解脱了出来,有太多的闲暇要打发。按瓦特的说法,英文小说完全是从穷极无聊的灰烬里诞生的。而无聊至极正是我眼下在经受的折磨。

我跟几位热爱探险的植物学家商量好,搭乘他们的小船去马萨弗拉岛。然后我就到户外用品店REI稍稍放开手脚消费了一通。REI的货架上各种超轻便野营用具琳琅满目,洋溢着鲁滨逊式的浪漫气息,最特别的可算是不锈钢马天尼鸡尾酒杯,酒盏跟杯脚可以拆开来的那种,在荒野里可充作人类文明的某种标识。除了背包、帐篷和刀具以外,我还给自己配备了一些时新的特色商品:一个塑料碟子,碟边是用硅胶做的,翻起来就可以变成一只碗;一些维生素C片,用来中和用碘消过毒的水的味道;一条装在极小袋子里的超细纤维毛巾,有机素食者会用的冷冻干燥红辣椒,还有一把坚不可摧的叉勺。有人告诉我,天公不作美的话,我就有可能无限期地滞留在岛上,因此我还储备了大量的坚果、金枪鱼罐头和蛋白能量棒。
启程去圣地亚哥的前夜,我去拜访了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遗孀、我的朋友凯伦。我起身告别时,她出乎意料地突然问我是否愿意带一些大卫的骨灰去撒在马萨弗拉岛上。我回答说愿意,她就寻出一方做成微型书本模样的带小抽屉的古董木制火柴盒,盛了些骨灰进去,说她深感欣慰,因为大卫的一部分将安息在那座荒无人烟、偏僻遥远的岛上了。直到驱车离开她家以后,我才意识到,她把这些骨灰托付于我,对她或对大卫都是一种慰藉,当然也是在为我考虑。她知道(是我告诉她的),我眼下逃避自我的情形是从两年前大卫死后开始的。
当时我下了决心,不去直面心爱朋友自杀这个令人难以承受的事实,而是逃遁于愤怒与工作中。现在,我已完成了我的创作任务,就更难对这件事视而不见了,更何况他自杀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感到无聊、乏味,且对他未来的小说创作心怀绝望。我自己近来也感觉无聊到了极点:难道这是由于我没有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吗?我曾对自己许诺,完成眼下这本书以后,我就让自己把对大卫之死的悲伤愤懑之情宣泄出来。
不久之后,一月底的那个早晨,在大雾弥漫之中,我终于抵达了马萨弗拉岛上一处海拔三千英尺、名叫勺子的地方。我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笔记本、一副望远镜、一本简装版《鲁滨逊漂流记》、那本盛有大卫骨灰的微型书、一个装满野营用品的背包和一张无比粗糙的岛屿地图,没带烟酒和电脑。当然,我并不是独自爬上山的,有位年轻守林人为我领路,还有一头驴子驮着我的背包;在好几个人的坚持下,我最终还带了一部收发报机、一个已经用了十年的 GPS、一部卫星电话以及一些备用电池。除此以外,我孤身一人,与世隔绝。
......
(《更远之地》【美】乔纳森·弗兰岑/著,潘泓/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摄图网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傅小平